过去只有三种方法可以脱离肾移植等待名单。第一是从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中找到一个健康的人,完美匹配接受者的血液和组织类型,并且拥有他或她愿意放弃的备用肾。
第二是等待一个陌生人意外死亡,这个陌生人是一个合适的身体匹配,碰巧在他们的驾照上勾选了器官捐献。
第三是死亡。
但是后来医生们想到:拥有足够多的肾脏病人和足够多健康自愿的捐赠者,他们可以形成一个足够大的捐献池来促进比过去一对一系统更多的匹配。只要病人能找到捐赠者——任何捐赠者,即使是不匹配病人本身——他们也可以得到一个匹配的肾脏。
起初,这要求医生花几个小时仔细研究病人和潜在捐赠者列表中的血型和组织变化细节。然后,计算机科学家和经济学家参与了进来。他们构建的算法比人脑更优雅地执行这些复杂的匹配。现在,多亏了人工智能,一个人勇敢迈出一步,将肾脏捐赠给所爱之人——或者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可以开启一条拯救数十条生命的链条。
配对肾脏捐献是人工智能的伟大成功案例之一。这并不能消除工作,也不能抹去医疗保健中的人情味。它应对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解决起来比人类更快,错误也更少,结果拯救了更多的生命。自从2000年第一对肾脏交换手术开始以来,近6000人接受了通过算法识别的配对交换的肾脏移植。今天,大约八分之一从活体捐献者那里接受肾脏的移植接受者,通过配对交换与该人配对。
与此同时,配对肾脏交换也是人工智能局限性的一个完美例子。计算机只能做人类能教它的事情,而我们无法教我们不懂的东西。自从医学学会如何用捐赠肾脏替代衰竭肾脏以来的几十年里,我们仍在努力解决如何分配珍贵的少量肾脏的问题,这种分配方式让每个人都感到公平和满意,并且不会导致不希望的、意想不到的后果。人工智能可以识别出在生物学上彼此适合的潜在捐赠者和接受者;将来,它甚至可以权衡决定谁先接受移植的道德因素。但是首先,我们人类必须就这些应该是什么达成一致。
肾脏充当身体的过滤器。对于肾功能衰竭的人来说,透析基本上是从外部复制器官的功能,将病人未经过滤的血液排出几个小时,然后再泵回体内。20世纪中叶透析的发明使一种曾经是死刑的疾病变成了一种慢性但可控制的疾病。
第一个门诊透析中心——西雅图人工肾中心,于1962年1月开业。由于每个病人每周都需要在机器上进行两次12小时的治疗,所以该中心在头两年,只能接受大约2000名当时有资格接受透析治疗的美国晚期肾病患者中的10名。
为了将利润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该中心组织了一个由七名公民组成的独立委员会。第一个接受和政策委员会——或后来被媒体称之为“上帝委员会”——由一名律师、牧师、银行家、家庭主妇、州政府官员、劳工领袖和外科医生组成。医生为他们做了一些决定:45岁以上的病人没有资格,儿童也没有资格,因为医生担心这个手术可能会给他们带来精神创伤。除此之外,委员会可以自行选择大约四分之一符合条件的申请患者。
根据1962年《Life》杂志的一篇文章,该匿名委员会成员会考虑申请人的年龄和性别,以及是否已婚还是有孩子。他们会考虑申请者的情绪稳定。他们会看申请者赚了多少钱,以及他们存了多少钱;他们的教育水平、工作、过去的行为和未来潜力。他们决定,既然开发这项技术的研究是在华盛顿州资助的机构进行的,那么只有华盛顿居民会被考虑,因为支付治疗费用的是该州的税收。
这篇文章称委员会成员作为“思想高尚、善良的公民”面临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们也是人类,而作为人类,总会受到有意识和无意识偏见的影响。他们是根据医生写的病历做出决定的,而医生会有意识和无意识的偏见。
该委员会的七名成员是美国太平洋西北地区中上层阶级的一部分,他们的讨论(至少是那些公开发表的)暗示了对那些似乎分享他们的地位和价值观的病人的好感。《Life》杂志中从来没有提到种族,但是很难想象,在一个仍然严重隔离的社会里(仅举一个例子,当时98%的华盛顿州员工是白人),有色人种并不在这些代表的考虑之中。
他们的讨论预示了一个问题,在原始的肾脏治疗机被更先进的技术超越之前,这个问题将会持续很久。即使一群人一致承诺尽可能做最好的事情,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到底什么才算是最好的东西?
当上帝委员会发布痛苦的决定时,其他地方也在进行治疗肾病患者的类似工作。
医生于1954年在波士顿的Birgham and Women‘s Hospital进行了第一次成功的肾移植手术,通过外科手术从一名23岁的男子身上取出一个器官,移植到了他的双胞胎兄弟身上,这位接受者又存活了八年。
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血液和组织分型的发展使得医生更容易识别捐赠者和接受者之间的成功匹配,免疫抑制剂药物的改进大大降低了移植排斥率。今天,一个已故捐赠者的肾脏在接受者体内会持续工作8到12年,而来自活体捐献者的肾脏平均寿命为12到20年。
1972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签署了立法,扩大医疗保险范围,将所有肾衰竭患者的透析包括在内。透析并没有治愈他们,但是它让更多的人在等待和希望肾移植的时候存活了更长时间。从那以后,美国需要肾脏移植的人数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可用的供肾数量。
根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的信息,截至撰写本文时,美国有114554人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94980人——83%——正在等待肾脏移植。
1968年的《统一解剖捐赠法》在美国建立了一个标准程序,通过这个程序,人们或他们的近亲可以授权死后捐赠他们的器官。但是,即使美国每个人都是注册器官捐献者(目前的比例是54%),也没有足够的肾脏来满足需求。只有不到2%的人的死亡方式能够使他们成为合适的器官捐献者。一个人死后器官仍然可以移植,氧合血液必须持续泵送通过它们,直到依靠外科手术从体内取出。在采摘手术前,已故捐赠者通常被宣布脑死亡,并被连接在呼吸机上。
幸运的是,由于大多数人生来就有两个功能正常的肾脏,且只需要一个就能存活下来,所以活着的人可以捐献肾脏。由于活体捐献者的肾脏寿命往往比已故的更长,所以对于需要移植的人来说,找到活体捐赠者通常是理想的结果。
虽然所有手术都有并发症或死亡的风险,但绝大多数肾脏捐献者在腹腔镜手术后仅仅需要在医院呆两三天,随后是另外四到六周的恢复时间。剩下的肾脏会发育以补偿捐献的肾脏,捐赠者通常会继续过着正常的生活。
当然,向你的兄弟姐妹申请器官不是一件小事。但是找到一个愿意捐赠的人通常是这个过程中最简单的部分,因为许多病人和他们的家人都会发现无法匹配器官。
佛罗里达商人Neil Emmott在2001年被诊断患有多囊肾疾病,一种可能导致肾衰竭的遗传疾病。他的妻子Lisa Emmott说,这个消息是“意想不到的和毁灭性的”。在被诊断出时,Neil38岁,Lisa27岁,这对夫妇结婚还不到一年。到2016年,他们有了两个年幼的女儿,Neil的病情恶化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医生建议他考虑移植选择的地步。
Lisa自愿立即捐赠。她很健康,和他拥有相同的血型,所以她认为自己是一个可行的候选人。但是器官捐献不仅仅需要血液和组织匹配。对捐赠者需要进行彻底的筛选,心理或社会经济问题可能会使他们的捐赠复杂化。Lisa得知,她的肾动脉形状的一个良性异常——肾动脉是运送血液进出肾脏的静脉——使她丧失了资格。Neil的弟弟作为替补出场,但由于一些小的医疗问题也被排除在外。这家人感到很伤心。
“需要器官是一个可怕的事情,”Emmott说。这时,这个家庭决定寻求市场。
人体器官“市场”的想法令人毛骨悚然。它们不是商品:美国法律明确禁止出售人体器官。但是从经济角度来看,市场就是任何想要东西的人找到可以给他们东西的人的地方。这个不仅仅依靠价格来分配资源的市场被称为匹配市场。约会池是匹配市场的一种类型(假设没有钱被用来交换友谊);想要肾脏的人和愿意捐献肾脏的人也是如此。
当市场很“厚”或有很多参与者时,市场工作得最好。在肾移植的最初几十年里,生病的人和他们的潜在捐献者被限制在他们自己非常薄弱的市场中。失败的匹配往往被证明是对重病患者的死刑判决。
但是如果市场可以变得更厚呢?
这个想法最初是在1986年德裔美国外科医生Felix Rapaport的一篇论文中提出,他提出了一个理论,即可以跨越两个自愿的供受体对移植肾脏:患者A从供体B接受肾脏,作为交换,供体A给患者B一个肾脏。
1991年,韩国首尔的医生们在肾病专家Kiil Park的指导下,在两个供体-患者对之间进行了第一对肾脏移植。四年后,世界上第一个配对肾脏捐赠项目在首尔延世大学医学院开启。潜在的捐赠者和接受者被输入数据库,然后由医生通过数小时的艰苦分析手动配对。1999年,瑞士成为下一个建立配对肾脏交换的国家,匹配了两对已婚夫妇,每对夫妇都有一个患有终末期肾病的配偶和一个愿意捐献肾脏的配偶。
2000年的一个晚上,在厌倦了向病人和他们的亲人传递令人心碎的消息之后,一位名叫Michael Rees的美国肾脏学家拖着几箱文件回家,花了几个小时仔细检查血液、抗体和组织数据,并比较患者列表。这项工作在精神上很累人。最终,他意识到自己没有可行的匹配——但是,如果捐献池更大,可以做成配对。与他的父亲Alan Rees一起合作(Alan是一名计算机科学家),Michael Rees创建了一个简单的计算机程序,将捐赠者和接受者配对,将人工智能引入匹配过程。
大约在同一时间,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Alvin Roth,也在修补肾脏匹配的解决方案。Roth专注于市场设计,专注于如何调整市场以修复供需失衡。他以前设计过算法来匹配新医生和住院医师项目,以及纽约市小学学生和高中学校。现在他把注意力转向肾脏。
Roth和他的同事Utku Unver、Tayfun Sonmez设计了一种算法,用于审查和分析潜在捐赠者和接受者的数据资料。它确定了捐助者-接受者配对的“循环”和“链”,其中一个人选择无私地将肾脏捐献给任何需要肾脏的人,从而在医院或肾脏交换项目登记的潜在捐献者和接受者中启动了一系列捐献。例如:患者B从利他捐赠者A那里得到一个肾脏,之后,捐赠者B感激地将肾脏捐赠给病人C。如果病人C有一个愿意捐赠的人,那么这条链可以继续延长,且没有真正的限制。不同于循环,链可以无限期地向前移动,而不必回去,通过为原始捐赠者的伙伴接受者找到肾脏来结束这个循环。
Roth、Unver和Sonmez觉得他们在做一件大事。2003年,他们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概述他们工作的论文,并发给了美国各地的肾脏学家。根据哈佛外科医生Frank Delmonico的反馈,该团队调整了他们的算法,并发表了一篇新论文,其概念帮助建立了新英格兰肾脏交换项目。该交换项目匹配了该地区14个肾移植中心的捐赠者和接受者。
起初,外科医生坚持在给定的循环或链中同时进行所有手术,这样任何捐赠者都不会在最后一刻退缩。这限制了循环或链中的患者数量,因为医院一次只能腾出这么多床位和这么多外科医生。经济学家和其他几位医生认为,这是不必要的限制。这不存在生物障碍:与心脏或肺不同,心脏或肺必须在离开捐献者身体后4到6小时内移植,而在找到新宿主之前,肾脏可以安全保存24到36小时。至于捐助链中薄弱环节的可能性,经济学家认为,在一个以愿意将肾脏给任何人的捐赠者开始的链中,如果捐赠者退缩了,任何接受者都不会束手无策,因为医生可以从注册捐赠者库中找到替代品。
建立第一个匹配算法的肾脏学家Rees,证明这是可以做到的。在一名28岁的捐赠者向一个需要帮助的陌生人提供了一个肾脏后,Rees组织了一系列肾脏捐赠,在八个月的时间里拯救了五个州10名患者的生命。
今天,美国多家医院都有自己的配对肾脏捐赠项目。此外还有三个更大的美国跨院肾脏交换项目:器官共享联合网络、国家肾脏登记处和配对肾脏捐赠联盟。英国、加拿大和荷兰设有国家交换项目,从印度到南非的医院都有配对捐赠发生。研究人员还推断,肺和部分肝移植也可能进行类似的交换,尽管还没有这种互换的系统。
2012年,Roth因其在市场设计方面的工作获得诺贝尔奖。他带Rees一起去参加了仪式。到那时,美国有2000人接受了移植,这是他们帮助创建的系统结果。此后又有成千上万的人得到了帮助。
Neil Emmott最终成为2017年肾链中的八个人之一,该肾链始于两位家人朋友前来为他捐赠。2018年8月13日,阿拉巴马州的一名妇女成为从2013年开始在全国范围捐赠链中接受肾脏移植的第100人。
今天,当医生正在寻找匹配肾脏捐赠者和接受者时,人工智能研究人员构建的算法搜索注册肾脏病人及其合作捐赠者的数据库,并根据器官采购和移植网络委员会和器官共享联合网络制定的加权标准列表来识别匹配。
这些算法同时评估所有可能在患者-供体库中进行的移植。匹配主要基于生物适应性,最难匹配的病人得到了优先考虑。这项技术衡量标准包括接受者在等待名单上的时间,他或她的年龄(儿童优先),以及需要肾脏的人过去是否曾经是活体器官捐献者。
这些算法帮助了成千上万拯救生命的手术。将来,人工智能不仅可以使用人类决定的标准进行匹配,还可以积极参与这个判断过程——理解人类的决策和价值体系,这样它就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断,决定哪些肾脏应该去哪里(这个决策将由人类医生审查)。在这一点上,限制因素与其说是技术,不如说是使用技术的人。
第一个问题是人类对人工智能在器官分配中的作用的焦虑。医院和器官交换机构甚至不愿意在匹配过程中使用“人工智能”一词。部分原因是研究人员称之为“人工智能效应”的趋势。正如牛津大学未来人类研究所所长Nick Bostrom所说,“一旦某些东西变得足够有用且足够普遍,它就不再被贴上‘人工智能’的标签。”
鉴于缺乏关于“人工智能”实际含义的公共教育,医院和交换机构对病人误解算法在识别潜在匹配方面的作用持谨慎态度,也许是害怕变戏法似的机器人冷冷地发布生死指令。
目前,机器不能决定哪些肾脏去哪里。人类可以这样做。今天的算法比人类更可靠,也更大规模地进行数学运算,执行人类已经做出的判断,但是它们并不了解为什么首先要进行计算。
“AI没有像我们一样对世界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它们不明白自己正在处理的数据是关于什么的,”杜克大学计算机科学、伦理学和哲学教授Vincent Conitzer表示。“它们没有这个人正在受苦的概念。它们并不真正了解一个人是什么。人类必须在某个时候介入进来。”
研究人员现在正在教机器从人类的角度来理解这些道德困境。今年,Conitzer和杜克大学的同事Jana Schaich Borg、Walter Sinnott-Armstrong、Rachel Freedman以及马里兰大学的John Dickerson,一起发表了一篇论文,其中他们向研究对象展示了数百对假设的患者概况,并询问每对中哪一个应该得到一个可用的肾脏。这些假设的患者档案并没有列出算法处理的血液和组织数据,而是列出了一些事情,比如患者饮酒的频率,以及他们过去是否患过癌症。研究人员随后将受试者的选择反馈给一种算法,并学习如何根据这些模式选择“正确的”肾脏接受者。就像人类受试者一样,人工智能偏爱更年轻、更健康的病人——这是一个机器根据对人类价值观的了解做出决策的例子。
虽然可以教机器按照我们的价值体系进行匹配,但是我们并不总是明白自己的价值观是什么,或者很难将其作为一个整体达成一致。人们并不总是知道他们想要优化什么,即使当他们认为这样做了,他们也常常不明白如何以不会导致意想不到的后果的方式去做。
例如,麻省理工学院的道德机器允许实验室网站的访问者玩他们必须选择的游戏,在一个又一个假设的情况下,无人驾驶汽车在面临两个可怕的选择时应该选择杀死哪一组汽车乘客或行人。在经历了一系列令人反胃的场景之后——是的,我宁愿汽车碾过一个孕妇,而不是五个无家可归的成年人;不,如果这意味着杀死五名成年乘客,我不会为了躲避两个孩子而突然转向——这一游戏揭示了它在你的选择中确定的模式,以及你的反应如何与其他玩家的反应相比较。
这些信息可以揭示出人意料的后果和令人不快的未被承认的偏见。例如,你可能会了解到,你的决定不成比例地导致了比女性更多的男性死亡,或者你倾向于比游戏中的一般玩家更看重遵守交通规则。
在肾脏问题上,就是采取表面上公平的原则,即肾脏应该给予那些在接受肾脏后可能会有最多寿命的人。在计算机能够计算潜在接受者的寿命之前,科学家必须为算法提供各种人群的预期寿命数据。但是这导致了一些问题。男人往往比女人早死。美国黑人比任何其他种族的美国人死得更早。2015年,一位65岁的美国白人妇女可能会再活20.5岁,比同龄的黑人长4年。虽然是从良好的意图开始,但最终却导致了系统的种族和性别歧视。
“在经济学中,我们谈论不可能性定理。有些东西你可能想得到却无法得到,”Roth说。“当你分配稀缺资源时,你不能把肾给一个人而不把它给另一个人。计算机不会从各个方面减轻人类的负担。”
人工智能没有造成这些道德困境。人类委员会为分配肾脏的最公平方式而不断苦恼;人类司机仍然不得不在方向盘后面做出可怕的紧急决定。机器可以在几小时甚至几分钟内模拟出人类判断的结果,这些结果原本可能需要数年才能发现。从长远来看,这可能会有所帮助:如果一个计算机模型能够证明特定的肾脏分配政策会对某些群体造成不相称的不利影响,那么医生可以在任何人实际受到伤害之前取消这项计划。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乐于让机器参与生死抉择。
道德机器教给玩家一些西雅图上帝委员会很久以前学到的东西:必须选择拯救哪一条生命,知道这个决定会导致别人的死亡或痛苦,感觉很可怕。这部分是人工智能所无法帮助的。人们可以找到组装椅子的理想方法,然后将这个过程传授给一台能够完美组装成千上万把椅子的机器。但却没有完美的方法来决定谁生谁死。
 电子发烧友App
电子发烧友Ap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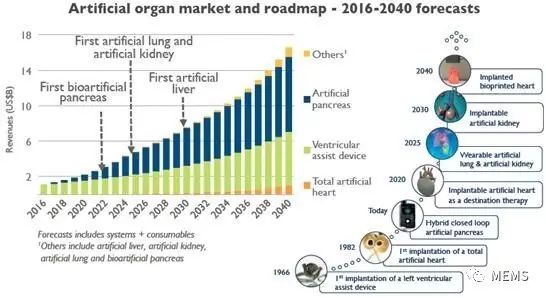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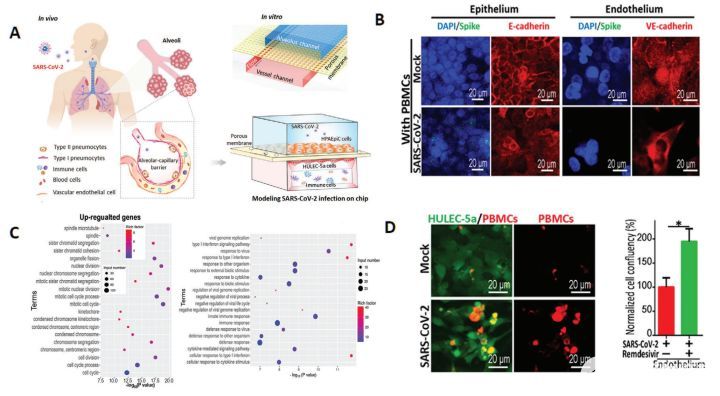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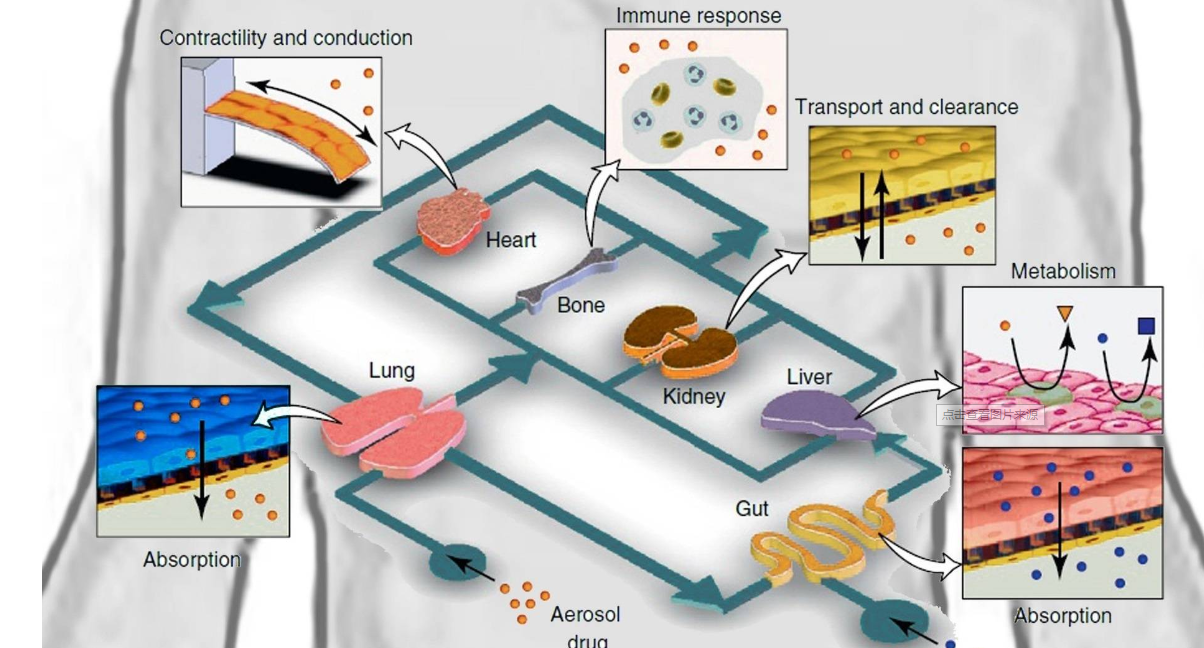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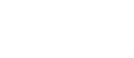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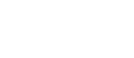





评论